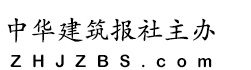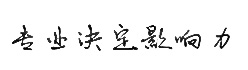跨越百年的鄉村建設行動,在近兩年獲得了空前關注。新一輪“鄉建熱”掀起,在新時代背景下,以更廣闊的內涵,呼應著鄉村振興的多個維度。
懷著好奇,記者踏上了一趟生機勃勃的旅程,足跡跨越蘇南、蘇中、蘇北,鄉村的蘇醒與新生,變與不變,令人欣喜。在昆山尚明甸,從上海過來創業的元蓁齋老板王鐸,熱情地展示店里冬奧村同款咖啡機器人;在網紅村牛角淹,磨盤、石磙成了“沉浸式文旅項目”,孩童們樂此不疲地復習父輩的勞作記憶;在宿遷來龍鎮豐莊社區,記者被淳樸好客的村民請進家門,欣賞他們窗明幾凈的新居,聊心中美好生活的模樣……借著這一波“鄉建熱”,鄉村在新起點上重新出發——它們將往何處去?
鄉土文化
水韻蘇鄉的新生起點
特色田園鄉村是江蘇的名片,特色文化又是江蘇特色田園的標識。早于2017年江蘇開啟特色田園試點,常州溧陽最先在一片空茫中想象現代田園的模樣,它的先行探路,使江蘇鄉建的邏輯鏈逐漸彰顯。
這也太美了吧!緊靠曹山旅游度假區的溧陽上興鎮牛馬塘村,是江蘇省城鎮與鄉村規劃設計院的得意之作,用“風景如畫”形容并不過分。除了沿用江南村落標志性的粉墻黛瓦作為主符號,牛馬塘的美還有一種特別的精致和具象。
比如,當地特產紅薯化身為五顏六色、憨態可掬的卡通形象。單是一面院墻就使用了規則的磚石、不規則的亂石和多種磚色的混搭,且輔以瓦片精巧堆疊出來的鏤空效果。村路也很值得賞味,用當地出產的鵝卵石收邊,增添了幾分平仄感。鵝卵石小道旁,有時會砌一道矮墻作為隔斷,那頭是錯落有致的藍花草、石榴樹,在夏末秋初的微風中搖曳。
溧陽市住建局原副局長韓金紅帶著記者逛村,熟稔得就像回家。在溧陽近十幾年的鄉建進程中,韓金紅的作用不可忽視。憑著對“何為鄉村”的理解、對鄉土特色的審美直覺,她提出“用地方材料打造地方特色”的鄉建思路——而那時,全社會還沒有形成“讓鄉村葆有鄉村模樣”的共識。
2005年,靠近溧陽南山竹海的戴埠鎮李家園村入選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試點,韓金紅每天“跑村”,除了感嘆鄉村的原生魅力,也為那些不搭調的“違和感”遺憾。李家園有豐富的竹資源和山澗水,自然稟賦優越,她尤愛那些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或逶迤爬升、或曲折下行,很有幾分山村的味道;當地村民卻喜歡用混凝土澆路,灰白的硬質路面。韓金紅提議,為什么不把鵝卵石壓在混凝土里,既完成路面硬化,又去掉混凝土固有的城鎮感?此舉果然可行。她又發動篾匠給各家各戶編竹柵欄,原本素面朝天的村居經柵欄點綴,有了雅的感覺,也保留了鄉土的俗韻。嗯,小景挺美的!
李家園村的鄉村實踐,其實啟示著鄉建的基本方法:花崗巖、柏油、真石漆,修剪得漂漂亮亮、整整齊齊的景觀樹,美則美矣,卻不是鄉村的語言。相反,一株鄉土樹木就算品種不高級、枝干恣肆歪扭,卻是當地氣候土壤的綜合產物,氣質天成,和村貌“百搭”。
宿遷蔡集鎮牛角淹新型農村社區,去年登上《人民日報》頭版,因為是“網紅”村,牛角淹有種靜謐中的熱鬧。全村最吸引人們駐足的,是一片精心保存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民居,事實上成為這座鄉村的“記憶之場”:有的房屋通體用紅磚壘砌,有的是茅草屋頂土坯房,走進屋內,秸稈的清香撲面而來。條凳、籮筐、舊櫥柜、落了鎖的木頭箱子……時間的履痕被一一封印,彰顯出當代鄉建者對村莊“小歷史”的敬重。出門一抬眼,孩童們有的推著石磙嬉戲,有的和媽媽、外婆“合作”推磨,興致勃勃地感受與這片空間相聯結的傳統生活方式。
鄉土文化是村莊生長的原點,這一觀念被越來越多的鄉建參與者認同。說起北華翔——我省第一批特色田園村、如今的昆山名片,省城鎮與鄉村規劃設計院規劃一所所長葛大永表示,解決經濟先發地區的村民對自身鄉村文化、本土審美的認同與提升問題,是他理解這個項目的核心著眼點。
進駐北華翔時,規劃設計團隊看到一排排裝點著羅馬柱的農房,有點哭笑不得。選了兩三棟農房試點,先是苦口婆心和村民溝通,又帶著村民代表外出考察,最后終于對農房上的歐式元素做出了盡可能經濟、安全和美觀的調整——看到現實版“夢想的家”后,村民們開始有點認同“國風”了。除了恢復粉墻黛瓦,團隊也竭力尋找北華翔自己的特色——臘肉文化!這里四面環水、昔日出行困難,先民們便學會制作方便貯存的臘肉。很快,臘肉的符號得到了巧妙的顯像化處理:村口一條老木船,船上堆著幾只舊腌肉缸,點綴以鄉土植被和村名logo,既有鄉風俗韻,又有現代的設計感。村上的臘肉產業鏈借此復蘇和裂變,三產融合的趨勢逐漸明顯。
“哦,原來傳統的就是美的啊。”出名的北華翔吸引各路資源要素涌入,村民有機會以外部視角重新打量熟悉的故土——通過融入他人的空間認知,實現本地人的“認同重塑”,喚起他們對鄉土文化的自豪和熱愛,也是鄉建中微妙而重要的一環。
究竟何為文化?省城鎮與鄉村規劃設計院黨總支書記、副總經理閭海的理解是,對鄉村而言,生產生活的方式、倫理秩序與觀念,才是更加本體的文化。“而非那些淺表性的,哪家院落里有好看的花紋圖樣,就拿來復制粘貼,文化的涵義不是這樣的。”
記者抵達泰州淤溪鎮周莊村時,是傍晚六七點鐘,千垎田園里,日間吸滿天地精華的玉米稈于曠野中釋放濃郁的香氣。村子依水而建,房屋密集,渡船靜臥,拱橋安謐,時有村民在水邊浣洗衣物,一派典型的里下河水鄉特色。第五屆紫金獎·建筑及環境設計大賽的一等獎作品《千垎周莊——里下河農耕記憶,“垎”的復興與猜想》,正是通過抓住當地的“垎田”農業文化遺產,扭住了鄉村運行與生長的內在邏輯。
前期調研時,南京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小城鎮與鄉村規劃分院院長張川就發現,周莊村缺的是新的出發點和動力:村民們普遍覺得生活水平在提高,但為閑置的農田感到可惜;提起當地出產的芋頭、茨菰,又是滿臉自豪。張川于是沿著村民的“心病”回溯當地的農耕方式——為應對里下河地區的水患頻仍,先民們在此挑土筑田,壘出大片高企于水面的垎田,這樣的農耕方式實則規定了一整套的生產生活細節。
比如,村民們劃船去種田;在水邊進行交往;灌溉時在竹竿一頭綁上瓢狀容器,容器里盛滿水,然后用力甩竹竿——摸清了這里獨有的DNA后,村里整理出了大片垎田,新的可能性便在村莊的固有邏輯上延伸。張川解釋,“千垎”即垎的一千種可能性,它可以是村民的一方菜園,是市民和村民交流的淘寶市集,是游客體驗農耕文化的場所,是“加速時代”里的“歸園田居”——結合現代生活的豐富需求,傳統的垎田將搭載無窮的內容和形態。
“看上去很美”背后
有鄉村強勁的內在生長
鄉村明顯變美了!這次下鄉,記者時有驚艷感:漫步鄉間就像移步換景,隨便一幀風景都惹人駐足,都值得被定格留念。
“但是,我們是要把鄉村做成一道盆景,還是可生長的大樹?”閭海拋出了一個問題。近十年,江蘇通過大力推動“設計下鄉”,包括舉辦鄉村創意設計大賽、把鄉村項目納入設計大師評選標準等,使一大批城里的設計師和鄉村有了深度連接。在長期的陪伴式、在地化服務的過程中,閭海發現,比“答題”更難的,是凝聚各方力量“把題目出好”,也就是鄉村究竟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在鄉村振興的多維愿景中,“產業興旺”是尤為關鍵的一環。在探索鄉村產業發展的路徑方面,北華翔的實踐很有代表性。
漫步于這座詩意盎然的現代田園,已無從想象金華村(北華翔所屬行政村)書記丁新良描述的舊時情景:村民得劃船去種“隔江田”,因為生活苦,外村姑娘嫁過來又跑了回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昆山經濟的騰飛為鄉村帶來機遇。承接經開區的需求外溢,村里建起標準廠房,靠租金壯大村集體經濟,同時埋下污染隱患;2017年進入特色田園試點后,當地狠心騰退了村里所有的污染企業,立志把“美麗”做成發展的增量。如今,北華翔騰籠換鳥的效果彰顯,“一廳多園”的格局已然形成:“一廳”是集納多重功能、開門揖客的田園客廳,“多園”是桃園、櫻花園、科普菜園、兒童樂園、咖啡廳、轟趴館、民宿等農文旅融合業態的疊合。
“我們北華翔人的性格很外向,無論你在村里有沒有房,這里都歡迎你來住。”丁新良笑言。
“看上去很美”的背后,是鄉村強勁的內在生長。昆山著名的“江南圩田·鄉野硅谷”尚明甸,距昆山德國工業園10公里,距上海虹橋站35公里,資源要素的集聚促使傳統的民宿經濟在這里提早轉型:民宿老板們來這兒創業,更來這兒生活——只不過把“家”共享了出來。
民宿七玖年的老板是一對上海夫妻,為了這間民宿投入了700多萬——因為是打造自己的家,所以不惜工本。和老板聊天,會發現更高階的民宿如今售賣的不僅是物理空間了:民宿老板的“人”本身,他們率性自然的人生觀念,在裝修、侍花弄草方面的審美品位,甚至,他們收養的7只貓咪,都成了這片小天地默默給予客人的東西。
“元蓁齋有一個智能咖啡機器人”是尚明甸的新鄉村傳說。元蓁齋的老板是三個上海女孩,為了把一杯手沖咖啡做得分毫不差,“剁手”幾十萬“拔草”了北京冬奧村同款咖啡機器人,到手后發現這錢花得簡直不要太值——解放了老板,讓她們有更多精力服務客人。
當前,民宿經濟暴露出同質化的短板,元蓁齋找到策略,給民宿做加法。老板王鐸是專業的心理咨詢師,見多識廣,想法也多:依托店里茶文化、咖啡文化、日式枯山水等不同的風格單元,她想做“民宿+”,在住宿外疊加心理輔導、冥想、禪修等多重功能,幫都市人慢下來、靜下來。“心靈修復是需要場域的,燈紅酒綠的都市不可能提供這種感覺,但尚明甸具備了這一點。”
并且,王鐸對鄉村發展進程中,如何處理“現代”與“鄉愁”的關系、如何重塑鄉村交往格局,都有思考:城里人、當地人,對鄉村的需求都是“既要也要”,要藍天白云、詩和遠方,也要全面的基本公共服務、現代化的便利生活,故元蓁齋有舊磚瓦墻、榫卯結構涼亭,也有咖啡機器人和可加熱的智能馬桶。城里和當地兩套生活方式、生活標準的相遇,又往往形成一種交往和學習。
別忘了,尚明甸還是一片棲于圩田的“硅谷”。鄉伴文旅集團負責尚明甸的運營,目前這里已吸引18家高科技企業注冊。工作的形態在這片鄉村發生了變化:這兒沒有寫字樓、格子間,卻有健身房、游泳池、動漫墻繪和360度無死角的鄉野風光,還能隨時遠眺網紅打卡地——圩田里的昆曲人物稻田畫。科創和人才要素的涌入又顯見地提升了村子的活力。在SOSO Coffee歇腳時,記者羞愧地發現這兒沒有閑人,年輕白領們全都對著電腦凝神辦公——城鄉融合的美好遠景在這里提前變現。
南京溧水李巷也有驚喜。抗戰時期,李巷村是“蘇南小延安”;如今,“紅色李巷”有了更多名片:全國鄉村旅游重點村、江蘇省委黨校培訓基地、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及各大單位開展黨性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陣地。在這里瞻仰陳毅、江渭清等新四軍將領的故居時,人們的目光無法不被房屋的外墻吸引:那是一張張坦然接受時光洗禮的無法偽飾的“臉”,清晰裸露著一輪輪修補的印痕。走出時空隧道,撲面而來的又是人氣興旺的鄉村新景——以“舊”帶“新”,紅色李巷就這么款款走出了“歷史深巷”。
李巷究竟做對了什么?該項目主創、東南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的設計師李竹概括了幾條思路。一是“建筑村落化”,也就是把人們印象里高大巍峨的紅色紀念展館做功能拆分,以一間間村居的散點合力完成展陳功能,“在田野、在古鎮、在鄉村承續紅色文化”成了李巷的特色。二是“轉角有人家”,歡迎老百姓留下,再把新的脈絡織入村落原有的肌理,村民想致富創業就有了家門口的機遇。這里的公共空間也定位于“主客共享”,一片片檐廊白天是游客休息的地方,晚上就成了村民跳廣場舞的地盤。凡此種種,其實都是刻意規避關門售票、與外隔絕的景區思維,把紅色資源的打撈融入鄉村振興的總體布局。
——從紅色李巷今日的盛名,追溯當時的紙上藍圖,才發現,鄉村的一切生長都有跡可循,鄉村的一切發展都需要精心設計。
鄉村“高光時刻”來臨
最終要做“時間的朋友”
平心而論,昆山、溧水、溧陽的鄉村作為大城市的腹地,天然擁有更多機遇,而在蘇中蘇北,鄉村的發展視野受到局限。和宿遷牛角淹的村民閑嘮家常,大爺遺憾,說牛角淹去年火了,今年的熱乎勁兒就有點消退。“網紅”之后如何“長紅”,如何拓寬產業形態、農民增收途徑,是牛角淹面對的新難題。在蘇北某村走訪,發覺村民的愿望很樸實也很“小”——臨鎮村民在家門口就能打上工,就足以讓大娘的眼里燃起羨慕的光亮。
深度變局中的鄉村,也面臨著移風易俗的難題,考驗著鄉村治理的智慧。在一些新型社區里,光是村民私建違章、亂扔亂放,就夠讓村干部頭疼了。紅白喜事的人情開銷,制約著“生活富裕”目標的順利實現。基層減負還須落到實處,“匯報材料裝了三個檔案盒,上面還嫌臺賬太少”——又如何輕裝上陣,帶領鄉村奔跑?
然而,眼下又是鄉村從未有過的高光時刻。溫飽過后,村民對美好生活滿懷具體想象,村干部渴望在鄉村天地大施拳腳,在外游子、鄉賢、社會力量與資本紛紛注目鄉村,城里人期待“小隱于野”、在鄉村感受“從前慢”——多重因素推波助瀾了當前的“鄉建熱”。那么,鄉建還能做什么?
首先應該問,鄉建應該是什么。服務旅游的鄉建立場,已逐漸糾偏為主客共享。大拆大并的鄉建方法,被“微介入”“微更新”或曰“有機更新”“漸進式更新”取代,更強調保留村民與土地的血脈糾纏,更尊重鄉村空間形式與生活模式的關聯形態,更關注減少成本、建立容錯糾錯的健康機制。
在泰州周莊村,讓記者驚訝的是,除了涼亭等公共空間的打造,這個備受好評的紫金獎作品幾乎看不到明顯的設計痕跡,有時甚至是“反設計”的。比如,一棟民居以中式大門混搭歐式欄桿,就那么風格雜糅地矗立在路口,但違和感從心頭升起后,又很快化作會心一笑。其實,鄉土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發生巨變,保留“時空壓縮”形成的真實駁雜,也是一種鄉建之道,這背后的深層用意一如張川所言,是“要讓鄉村真正成為與城市對等的生態系統”。
其次應追問,鄉建不應該做什么。復盤和反思近年來的鄉建項目時,閭海發現,一些名噪一時的鄉村網紅建筑衰敗了,根源是和當地的需求不匹配,無根也就無法生長。有村干部抱怨,設計師不了解鄉村,改造后農房的院落太小,村民們只能又把農具堆到了大路上。又如,一些地方對鄉土特色的理解止于張貼文化標簽——葛大永直言,文化的顯像化不過是“記住鄉愁”最簡單的第一步,文化只有變身為產業,可購、可食、可思、可感,才能活在當代。
“鄉村是我們每個中國人的老家。”曾寫下《一個人的村莊》的著名作家劉亮程這樣說。但其實,鄉村不僅是中國人心靈意義上的“老家”,也應是物理意義上可供樂業安居的現在、永遠的家。
眼下,大地已蘇醒,鄉村的心跳澎湃明晰。丁新良激情暢想北華翔的“近未來”:有朝一日,北華翔會吸引更多人到訪,他打算一張藍圖繪到底,給北華翔買份整村保險,讓每個慕名前來的客人賓至如歸、解除后顧之憂;
紅色李巷這么有名,李巷村的產業發展如何配得上它的名氣?南京溧水石頭寨村(李巷村所屬行政村)第一書記余謝介紹,下一步李巷將“小步快跑”,壯大村集體經濟、提升農作物附加值,也要讓紅色李巷這個“網紅”吸引人們“N刷”;
宿遷來龍鎮豐莊社區眼下正搭建“社區黨委—網格黨支部—黨員中心部—片區黨小組”的四級黨組織架構,想把鄉村治理之網織密織牢,同時融入便民服務事項。而早些時候,圍繞退役軍人、黨員干部、熱心群眾三大主體,社區已成立“戰旗紅”“黨徽耀”“豐莊風”三支志愿服務隊,營造村民互助體系,下一步的“小目標”則是瞄準鄉賢、能人大戶,把這些珍貴的鄉村發展資源擰成一股繩;
像李竹這樣的“外腦”,如今已是陪伴鄉村成長的活躍分子。9月8日這天,他把教學課堂搬到了李巷,請大四學生面對一個個真實的“客戶”——村民,傾聽他們的心聲和需求。鄉村需要更多青年關注,需要更多未來的鄉村設計師。
到2025年,建成1000個特色田園鄉村,1萬個美麗宜居鄉村——江蘇“十四五”規劃清晰寫下了對鄉村的承諾。當“特田”遍地開花,建設特色田園鄉村示范區,使相鄰的“特田”互補共生、錯位發展,是江蘇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鄉建不是城建,鄉村的生長需要等待。”在這趟難忘的鄉村之行里,幾位鄉建專家都向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這也恰是劉亮程理解的“鄉村哲學”。鄉村衰落是一道困擾全世界的難題,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我們需要歷史的“雄心”,推動關注鄉村的各股力量碰出最強的合力、找到最好的方法,也需要歷史的“耐心”,靜待鄉村成為時間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