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登亮,是全聯石材業商會副會長、貴州省石材協會會長和貴州玉林石材掌舵人。
初見王登亮,衣衫簡樸,身形瘦小,很難讓人與他豐富的人生經歷聯系起來。他任過教師,做過政府部門職員,開過煤礦,當過村主任,現在做石材礦山開采及相關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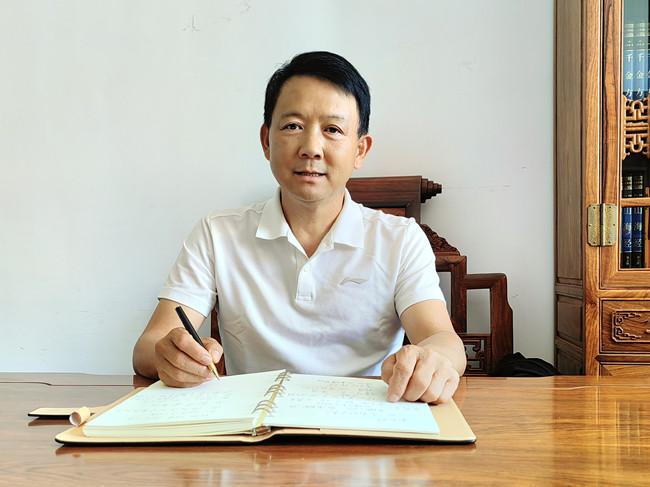
前不久,在貴州省安龍縣一個山坳中,王登亮的辦公室里,與他聊起這些過往,他的質樸,他的堅韌,他對家鄉的深厚感情,無不帶著貴州大山的濃厚氣息。
想多給別人幾個“飯碗”,自己捧著“鐵飯碗”卻失業了
記者:許多人聊起您時,說您是一個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特別是在幾十年前貴州這樣的貧困地區,您敢于砸了自己的“鐵飯碗”,我想知道,您的勇氣來自哪里?
王登亮:這得從當時的實際情況說起。我也是山里長大的人,初中畢業后,考上了安龍縣的師范學校,畢業就分配了工作,從事教書職業,后來又調到了縣教育局工作。
上個世紀90年代,教育系統興起發展第二產業,為教學提供一些資金幫助,各地教育系統開始興辦企業,需要有人去“吃螃蟹”。如您所說,大家捧著“鐵飯碗”,都不愿輕易去冒這個險,擔心回不了原來的崗位;但我認為,這樣做可以幫助到更多鄉親,于是就毫不猶豫地去了。
1994年,我領頭開辦了第一個煤礦,經營了10年。2004年,政策發生變化,我本可以回到教育局,可擔心丟下這些礦工咋辦?回到教育局,我一個人有飯吃,繼續做煤礦,大伙都有飯吃。就這樣,我從教育局離職出來,成了自由職業。
記者:后來,您連煤礦也放棄了?
王登亮:煤礦生產對安全和技術的要求極高,但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和技術更新,才能對礦工生命實現最大的保障。顯然,我很難完成這樣的使命。如果我繼續持有礦山,或許個人能賺到不少錢,但是比起礦工的生命,這是毫無意義的。
所以我認為,政府對煤礦進行整合技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積極迎接并主動放棄了煤礦的個人權益。
記者:有人說,從教育局離職,您的“鐵飯碗”沒了,放棄煤礦,您的“金娃娃”沒了。為了別人,您自己卻失業了。人到中年,有沒有過后悔,或者擔心出路?
王登亮:坦率地講,沒有后悔,也沒有擔憂,這兩次放棄職業,都是我主動的,并非被迫。再說,我有做產業的經驗,有管理企業的經驗,何懼之有?
我是在貧窮的環境里長大的,對貧窮有“免疫力”。我不怕窮,失敗了大不了就是窮嘛。
記者:這種勇氣很讓我敬佩。后來您為何進入了石材行業?
王登亮:安龍“木紋石”的發現,要感謝唐楚薦、張應發兩位石材人前輩。我失業后,在家里休整了兩年,但終究是要找個事情做。
2009年,國家各類建設如火如荼,我發現石材有很大的市場需求,“木紋石”市場潛力無限,于是,我邀約合伙人買下了一個石礦,加入了石材人的行列。
記者:貴州是個石材大省,您現在是貴州省石材協會會長,從某種角度說明您的企業是成功的,也是行業對您個人的認可。您認為這主要歸結于什么?
王登亮:是利益共同體或命運共同體吧,一個人不能心里只裝著自己,如果只裝著自己,那最多只是做個生意,心里裝著別人,才是做事業。
我希望自己做的是事業。
做事業,首先要對父老鄉親有所幫助。我做石材,解決了400多人就業,公司里省勞模就有兩個,還有職工選上了政協委員,這比我自己得到這些榮譽還要開心。另一方面,就是要讓合作伙伴也能賺錢,也能養家糊口,不能當“周扒皮”。我始終盡量讓利給中間商,抱團發展,大家都成了命運共同體。
記者:在石材行業十幾年,什么讓您感受最深?
王登亮:感受最深的,是貴州大山人的苦,是貴州山區發展的不易。
最初,我們把石材開采出來后,是用背包背著走到市場上去,求別人幫忙推銷。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很久,直到“木紋石”慢慢廣為人知。
那時,公路還是沙土路面,只要有客戶過來看產品,我們就走路去接,或者找農用車去接,用盡各種辦法表達誠意,很怕條件太苦,客戶不敢來第二次了。
做了一塊“試驗田”,是為了盡力幫幫鄉親們,日子能過得好一點
記者:據說您為了幫助鄉親們過上好日子,在老家村子做過一塊“試驗田”?
王登亮:“試驗田”是大家的一種說法,實際上是一個產業項目。
我是安龍縣本地人,企業也在這里,我有家鄉情結。那個時候,國家還沒有全面發起脫貧攻堅,貴州也還沒有脫貧。我有錢了,鄉親們還窮,每次見到他們,心里就有些過意不去。于是,我就開始琢磨怎么改變這個狀態。
開始,我在經濟上經常資助他們,到了年底,就叫鄉親們來領錢,70歲以上老人和殘疾人,每個月發100塊錢。后來,我發現這不是長久之計,不是說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嗎?
記者:是這個道理。
王登亮:貴州交通不便,產業薄弱,這是貧困的根本原因。要富起來,還得有產業,還得因地制宜。
于是,我出錢帶著村里的干部到各地考察了很久,覺得養桑蠶比較適合村里的實際情況。我把這個想法跟鄉親們說了,他們積極性卻不高。為什么呢?投入哪里來,技術哪里來,銷售怎么辦,都是個問題。
記者:您是怎么解決這些問題的?
王登亮:第一,我把鄉親們的地都流轉了,給他們錢,旱澇保收,先解決了他們的后顧之憂。第二,種桑蠶需要的樹苗、蠶種、肥料,我全部買來送給他們。第三,技術人員由我出錢聘請。
此外,為了把產業做起來,四個村民小組的組長,我每人發500元的月工資,五個村干部,我每人發2000元的月工資。我對他們只有一個要求,要像國家干部一樣負責,必須把這個產業干起來。
之后我又投入了300多萬元,給村里建了一棟非常漂亮的辦公樓。又用一年多,用挖機把村里所有的路挖通了。至于蠶繭,我保底15元每斤回收,實際上后來我用了18元每斤來回收。
記者:整個村子都發展桑蠶,全部由您投入,這個負擔應該也不小吧?
王登亮:這的確是需要一些投入的。我流轉了2600多畝山地,水稻田留著,保障鄉親們有米吃。投入方面,樹苗錢共50多萬,每畝地的投入達2000多元。到了第三年,鄉親們都賺錢了,積極性就起來了,我就不用再給他們投錢了。
記者:現在產業情況如何?
王登亮:目前發展的很好,縣里看見效果很好,因勢利導,大面積推廣,僅安龍縣現在差不多就種了上萬畝,發展成了一個不小的產業了。當地政府為了把這個產業做好,還動員我做了幾年的村主任。
靠山吃山,不能坐吃山空,吃相太難看,就對不起老天的恩賜
記者:貴州多山,石材是典型的靠山吃山產業,目前全省石材產業的年產值大概有多少?
王登亮:高峰時期差不多達到100多個億元。貴州主要是采荒料賣,從2010年到2015年這段時間,路邊都停滿了拉石材的車,我們縣有一條路,基本上天天都要交警來疏通。但是這樣粗放型的發展,吃相不好看,對不起老天給我們的恩賜,如果不轉型升級,我們終將坐吃山空。
記者:您的擔憂來自哪里?
王登亮:貴州屬于喀斯特地貌,木紋石是一層一層的,不是說從上到下全部都是,中間隔離層是其它石頭,資源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貴州交通運輸是個短板,基本上是汽車運輸。石材產業的發展成本太高,利潤都撒在公路上了,真正用于地方經濟發展的收益卻很少。
還有環境保護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解決上面這些問題,就等于慢性死亡。
記者:您找到答案了嗎?
王登亮:答案就是學會真正的靠山吃山,讓山變成名副其實的金山銀山。
我們正在從兩個方面去破題。首先要珍惜資源,木紋石要走個性化、高端化、品牌化的道路。2010年,我們邀請國家建材設計院對木紋石進行了質量認證,結果顯示其含鈣和鎂,屬于環保的、無輻射的、低碳的產品,如果用到家裝里,對甲醛或者其它一些有害物質,能夠起到一些消除作用。也就是說,木紋石不僅是建材產品,還是健康產品。
木紋石在歐美深得消費者喜歡,價格也不低。未來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宣傳,提高認知,做出木紋石的附加值。
第二是產業轉型升級,做好循環經濟,深度發掘石礦的經濟價值。
記者:轉型升級、循環經濟,對普通人而言比較抽象,您能否說得具體一些?
王登亮:就拿我們石材開采的固體廢料(簡稱“固廢”)來說,它不但影響環境,還需要投錢處理。如果我們將它變廢為寶,變成錢,這是不是轉型升級,是不是循環經濟?
記者:能做到這一點嗎?
王登亮:我們做了很長時間的努力,基本已找到了方向。
開始,我們想平整石材開采后的土地,恢復成基本農田、經濟果林,或者做成石磚等,但都不具有操作性。后來,我們又把思路集中到了固廢的成分上,它里面含的鈣和鎂,都是人體需要的元素,在工業領域也有廣泛應用。
于是,2015年開始,我投入4000多萬元建設了一條試驗生產線,聘請技術人員組成研發團隊,在固廢中提煉鈣和鎂。
記者:這個研究是跨領域的,超出您專業的,我聽試驗車間的同事們講,開始研究這10年來,您都一直深度參與,為什么?
王登亮:首先這是一次深入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該產品的技術研究是超前的,是需要進行攻關,我需要了解詳細的情況。
最重要的一點,我作為貴州省石材協會的會長,要做固廢綜合利用的研發,是站在貴州整個產業發展的角度考慮,我必須對這個領域有非常透徹的了解,才能在整個產業的布局決策中,提出建設性方案。
記者:產品質量或性能達到了怎樣的標準?
王登亮:我們現在研發的就是鈣、鎂兩大系列產品。鈣可以做到納米級,鎂也可以做到高純度。
記者:整個貴州石材開采需要處理的固廢,大概有多大的規模?按照您這個設想,能創造多大的價值?
王登亮:以安龍縣為例,每年石材開采剩余的固廢大概有50萬噸,由此可以算一筆賬,處理1噸固廢差不多要投入100元左右,一次每年總共需要投入5000萬元。
固廢如何創造價值?具體來看,2.5噸固廢可提煉1噸碳酸鎂,2噸固廢可提煉1噸碳酸鈣。碳酸鈣現在市場上是800多元1噸,如果投入成本計400多元,也就是說提煉出的碳酸鈣每噸毛利有300多元,50萬噸固廢可提煉25萬噸碳酸鈣,毛利就是7500萬元,再加上省下來的固廢處理投入的5000萬元,一減一加,等于增加毛利1個多億。
如果全省推廣開來,將衍生一個新的、很大的產業。無論是經濟效益,還是創造就業,都是很大的成就。當然,這是理論數據,市場行情在不斷變化,但總體方向是對的。
記者:我所了解的情況是,不論是鎂還是鈣,各地都有生產。比如在廣西賀州,碳酸鈣產業已經規模很大,貴州如何參與這個領域的競爭?
王登亮:我們有三個優勢。一是變廢為寶,我們的原料是不用花錢買的,沒有成本投入,還解決了環保問題。二是后發優勢,產品起點高,碳酸鈣起點就做納米級,碳酸鎂起點就做高純度,這樣一來,市場競爭力就起來了。三是因為固廢里有高含量的硒、碳酸鋰,甚至還含稀有金屬銫和銣,只要進一步開發這些固廢,大山就是真正意義上的金山銀山,就能更多的造福于民。
記者:按照您的想法,如果把研究成果產業化,是否有困難?怎么解決?
王登亮:最主要的困難還是投資問題。現在石材市場低迷,靠做石材的收益來再投入,有很大的壓力,時間線也會拉得太長。
如果按照每年生產1萬噸普通鈣、1萬噸納米鈣、1萬噸金屬鎂來設計一個廠區,至少需要投資2個億。所以,得到政府對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視和扶持,以及社會資本的進入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如此,再難我們也得做,這是貴州石材產業的千秋大計,涉及成千上萬人的飯碗,更是鄉村振興的歷史使命。
記者:很多人努力奮斗,就是為了走出大山,您已經走出了大山,卻又回到了這里,一直在這里奮斗,您就沒向往過大都市的生活?
王登亮:我出生在這里,我的事業在這里,這里就是我的根。我對這里的山山水水和鄉親有感情,我覺得我的事業很有意義,我的生活很充實、很快樂。

記者手記
向中國石材人致敬
采訪完王登亮,很長時間,我都無從下筆。
對于從事新聞職業30多年的老報人來說,這種情況并不多見。
按照《中華建筑報》與全國工商聯石材業商會的合作共識,這次的“中國石材全聯行”大型新聞行動,旨在首次以新聞的視角,全面、深入、系統的講述一批中國石材好故事。
中國石材好故事,重點似乎在石材,這種慣性思維束縛了我的思考。
王登亮的石材企業無疑是成功的,在當前市場低迷的行情下,他的“木紋石”依舊供不應求,客商排隊等貨。可與他的善良、質樸、對家鄉深沉的愛相比,我卻被后者所深深打動。
這就是令我難以下筆的原因——我該寫王登亮的石材,還是寫王登亮的情懷?如果寫后者,會不會跑題呢?
王登亮的人生故事,把我帶入了近期眾多反映農村題材的影視作品中,無論是《綠水青山帶笑顏》《大山的女兒》《高山清渠》,還是《春風又綠江南岸》,我似乎在每部作品里,都能看到王登亮的影子。這些影視作品,反映了貧困地區的人們不向命運低頭的頑強抗爭,以及為了美好生活進行的史詩般的艱苦奮斗。
聯想到這一點,我才有些釋然——也許,這才是這次新聞行動的意義之所在——通過這些報道,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石材這個傳統產業的與時俱進,和這個大約只有千萬從業群體的博大胸懷,雖然他們天天跟冰冷的石頭打交道,可是他們的匠心,他們的情感,他們的擔當,他們的信念,同樣閃現著人性中撼天動地的偉大光芒。
這難道不是最好的中國石材故事么?
于是,我決定做這樣一篇“跑題”的報道,包括用了《王登亮:愛在青山綠水間》這樣“土氣”的標題。
以此文,向把嘉祥石雕愛到骨子里的杜運偉、向為了絲路石材重放異彩而殫精竭慮的王忠邦、向為了共同致富一擲千金的先行者王萬傳、向經營石材如經營人生一樣用情的王時峰,以及所有的中國石材人——致敬!(文/本報記者 袁然)


官方公眾號

官方視頻號

官方微博號

官方百家號

官方抖音號